輿情監測顯示民眾對政府專傢及媒體信任度低
捐款少瞭。徐駿繪
政府表態,不信;專傢解釋,不信;媒體報道,還是不信。曾經的“權威聲音”,許多人如今是將信將疑
公信力緣何被削弱?
除瞭自己,我們還能相信誰?
社評:中國社會面臨全面公信力缺失
政府、專傢及媒體等公信力受損,導致社會信任度不斷降低,在一系列熱點事件面前,老百姓成瞭“老不信”。
“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不信瞭” 日前,突然爆出的“郭美美事件”,讓多年來一直熱心公益事業的的張女士有些茫然無措。“以前覺得具有官方背景的紅十字會應是最安全的捐款通道,現在看來或許遠不完全是那麼回事。”盡管“郭美美事件”發生後,紅十字會作出瞭相應的澄清,但是張女士卻表示,給出的解釋缺乏足夠說服力,並不能完全讓人信服。此前,無論是汶川地震、玉樹地震,還是甘肅泥石流,張女士都曾通過向紅十字會公佈的賬號打款的方式參與公益。有時候,在一些公眾場所看到紅十字會設立的捐款箱,張女士也會拿出一些零錢投進去。但現在,她明確表示:“短期內我是不會再通過紅會這個渠道捐款瞭,因為在我心中它已失去瞭應有的信任”。
不隻紅十字會,近幾個月,接連曝出的慈善總會“尚德詐捐門”、青基會“中非希望工程”等一系列與公益慈善有關的事件,都深深刺痛著社會大眾的神經,直接導致瞭對慈善機構的信任度降低,捐出的善款驟減。據中國公益慈善網公佈的信息顯示,“郭美美事件”發生後,公眾通過慈善組織進行的捐贈大幅降低。3 5月,慈善組織接收捐贈總額62.6億元,而6 8月總額降為8.4億元,降幅86.6%。
其實,遭遇信任危機,慈善組織並非孤例。近年來,懷疑一切似乎已經成為瞭很多人的心理共識。中國社會科學院2011年發佈的社會心態藍皮書顯示,從總體上看當代中國人的精神狀態顯得生機盎然、活力四射。但與此同時,社會信任度正處於低值狀態,對北京、上海、廣州三市市民的調查結果表明,三市市民總體社會信任屬低度信任水平。
中央黨校社會學教授吳忠民認為,之所以會出現信任度不斷降低的局面,關鍵在於做為社會情緒穩定器的公信力出現瞭問題。“公信力就是公眾對公共權力及特定角色形象塑膠回收押出機|廢塑膠再生製粒機的信任度,體現瞭它們存在的權威性、信譽度以及影響力。”吳忠民表示,一旦社會公信力受到損傷,便會導致民眾對負面消息的接受度不斷提高,鑒別真偽的意識受到削弱,久而久之,便會造成較大面積的“信任危機”。
來自人民網輿情監測室(微博)的監測顯示,目前社會公信力下降導致的信任危機,以政府、專傢及媒體最為嚴重。不相信政府,不相信專傢,更不相信媒體已構成瞭當前社會上一堵亟待翻越的“信任墻”。
“從政府層面看,公信力損耗尤為明顯。”人民網輿情監測室主任輿情分析師龐胡瑞指出,當前一些政府部門或地方政府在突發事件面前試圖封鎖新聞和輿論,常常會進一步激怒公眾,直接導致公眾對政府發佈的信息不信任,讓政府為澄清流言、穩定人心付出瞭很大的代價。
此外,專傢及媒體的公信力也同樣受到瞭較大程度的削弱。在山西等地發生的地震恐慌中,地震局專傢一再被公眾當做調侃對象。還有一些養生專傢,更是來得快去得也快。
“通常情況下,政府、專傢及媒體的信任危機並非各自孤立,它們往往都是擰合在一起出現。”龐胡瑞說,現實中,一些政府部門在應對公共事件上的非真誠表態,往往難以第一時間解除大眾心中的疑惑,這時某些所謂的專傢便會站出來通過媒體管道發表一些非公正的言論,試圖平息民眾的質疑,但結果卻常常適得其反,引發連鎖信任危機。
“老百姓成瞭‘老不信’,為我們敲響瞭警鐘。”吳忠民表示,公信力的構建是一個長期過程,但是破壞起來,一夜之間就可能喪失殆盡。“如果不能有強大的社會公信力做保障,就難以形成有效合作的社會局面,這將極大地提高社會做事的成本,影響改革發展的順利推進。”
“權威聲音”,為何也被打問號?
社會轉型期,原有的行事準則很多已無法適應社會新的發展態勢。一些政府部門在公共信息的供給上“做得不夠好、應對不恰當”,部分專傢受利益驅使喪失瞭公正立場,影響瞭公信力
政府、專傢、媒體,曾被視為最有公信力的群體,今日緣何信任不再?
“總的看,出現這種局面與社會發展的大進程密不可分。”吳忠民認為,目前我國正處於社會的轉型期,利益主體多元,利益格局多樣,舊的規則體系已無法起到應有的作用,但是新的體系還沒有真正建立起來,仍處於真空期。“原有的很多行事準則,已經無法適應社會新的發展態勢,民眾的訴求也與過去有瞭很大的差異,當‘供給’無法有效滿足‘需求’的時候,公信力就會受到削弱,信任度降低就成為瞭一種必然。”
“供給”與“需求”的不匹配,在政府公信力的下降上表現尤為清晰。從政府的“供給”看,其對公信力的重視程度仍顯不足。國傢行政學院公共管理研究中心主任薄貴利表示,這種不足突出表現為一些政府部門和地方政府在這方面“做得不夠好”、“應對不恰當”。
“之所以‘做得不夠好’,關鍵在於這些政府部門、地方政府,依然將與老百姓的關系定位在管理者與被管理者。”薄貴利說。當前,部分領導幹部中間,仍存在著較為嚴重的官僚主義傾向和特權思想,對老百姓通常說的多,做的少,或說而不做。很多地方政府在政策、措施的制定和執行上,缺乏全面、深入、系統的調查研究,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甚至還將機構自身的特殊利益置於公共利益之上,與民爭利,從而引發民眾不滿。
“應對不恰當”則更多表現為在面對重大突發事件時,一些官員仍難以擺脫陳舊的思維模式,習慣於“捂”“瞞”的應對策略,不少地方該公開的信息不公開,這常常使得民眾因不瞭解事實真相而謠言四起,導致政府工作陷入被動。“對老百姓都不信任,又如何奢求讓老百姓信任你呢?”
在政府“供給”不足的同時,百姓的“需求”卻在與日俱增。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民眾對公共事務的參與度、對公共信息的知情權都有瞭更高的要求。“但是,目前政府和老百姓之間尚沒有建立完善的溝通協調機制。”薄貴利說,由於信息傳遞渠道不暢通,很多群眾無法通過正規途徑反映問題,以推動問題的解決,因此,一些人無奈之下便將獲得事實真相、表達自身訴求的希望寄托於網絡,通過互聯網表達不滿,質疑政府行為的真實性和公平性,這就會直接導致對政府信任度的大幅下降。
相較於政府公信力問題上的“內外夾擊”,曾被視為角色獨立、立場公正,能為民眾提供權威意見,為公共利益代言的專傢、媒體,其公信力透支的背後,則更多體現著社會轉型背景下,利益沖擊面前的一種迷失。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快速轉型,個別人依靠非正常手段富裕起來,過上瞭普通人難以企及的奢華生活,巨大的名利落差強烈沖擊著社會上各個群體。“專傢和媒體都是社會的一分子,在這樣的沖擊下很難獨善其身。”吳忠民認為,正是在賺大錢、出大名的驅使下,部分專傢急於求成,不再安心做研究,堅守學術良心,個別媒體也不再追求事實真相,而是淪落為瞭利益集團的代言人,逐漸喪失瞭公正立場,“一旦失去瞭嚴謹和公正,專傢、媒體也就失去瞭維護自身公信力的基礎”。
受損的廢塑膠熱熔處理|廢塑膠熱熔押出公信力,如何重構?
切實解決好百姓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對於損害公信力的做法實行最嚴格的處罰,提高失信成本;提高公眾辨別能力,避免先入為主
薄貴利認為,“權威聲音”的沉沒已經影響到瞭社會正常秩序的構建,加大瞭經濟社會改革的難度,因此必須引起高度重視,盡快從制度層面尋找長久出路,用心加以解決,否則未來將可能產生更加嚴重的後果。
“政府公信力是社會信任的基礎,因此重構公信力應首先從政府著手。”薄貴利建議,各級政府部門要真正從制度建設入手,切實克服消極腐敗現象、官僚主義和特權思想,積極構建服務型政府,切實解決好百姓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同時,加強政策制定的民主化、科學化和法治化建設,增強公共政策的公平性,“隻要各級政府部門能夠真正做到潔身自好、一心為民,那麼重新找回百姓的信任就不再是難事。”
此外,龐胡瑞也指出,重新找回政府的公信力,加大信息的公開力度,提升政府的透明度同樣必不可少。“無論是經驗還是教訓都表明,面對信任危機,主動應對比逃避拖延更理性,用心疏導比一味堵塞更管用,未雨綢繆比應急救火更重要。”他表示,隻要政府能夠切實推行“魚缸”式透明操作,全面保障老百姓的知情權塑膠熱融押出、參與權和監督權,讓公共權力真正在陽光下運行,曾經的“權威聲音”就一定能夠重新贏得民眾的信任。
令人欣喜的是,目前,各級政府部門已經在探索信息公開規范化、制度化的道路上邁出瞭重要的步伐。從信息公開條例的頒佈到新聞發言人制度的建立,從官網發佈信息到主動微博問政,各級政府部門正在一系列制度的硬約束下,通過認真傾聽民眾心聲,及時回應社會關切,有效引導社會大眾的情緒,慢慢找回失去的信任。
“專傢、媒體的公信力重構,同樣離不開相應的制度保障。”吳忠民認為,為瞭保證社會公眾在面對重大公共事件時,能夠獲得來自專傢、媒體及時、準確的信息和建議,也必須要從制度層面著手,建立維護其社會公信力的長效機制。一方面要建立相應的利益保障機制,使專傢媒體能夠有說真話的底氣,同時,也要建立必要的懲處機制,對於損害公信力的做法,實行最嚴格的處罰,提高失信的成本,隻有這樣才能恢復社會公信力,擾亂大眾視線的謠言才會不攻自破。
此外,薄貴利也指出,增強社會公信力,消除信任危機,也離不開老百姓自身素質的提高。目前,社會的焦慮情緒總體比較嚴重,很多人把懷疑權威作為一種情緒宣泄的方式,對於公權力總是會先入為主一概否定。因此,必須在全國上下大力開展公民教育,讓更多的老百姓知法、懂法,切實提高自身的權益意識和謠言鑒別能力,確保能夠對政府的行為和專傢言論進行正確理解,不輕信、不亂言。
捐款少瞭。徐駿繪
政府表態,不信;專傢解釋,不信;媒體報道,還是不信。曾經的“權威聲音”,許多人如今是將信將疑
公信力緣何被削弱?
除瞭自己,我們還能相信誰?
社評:中國社會面臨全面公信力缺失
政府、專傢及媒體等公信力受損,導致社會信任度不斷降低,在一系列熱點事件面前,老百姓成瞭“老不信”。
“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不信瞭” 日前,突然爆出的“郭美美事件”,讓多年來一直熱心公益事業的的張女士有些茫然無措。“以前覺得具有官方背景的紅十字會應是最安全的捐款通道,現在看來或許遠不完全是那麼回事。”盡管“郭美美事件”發生後,紅十字會作出瞭相應的澄清,但是張女士卻表示,給出的解釋缺乏足夠說服力,並不能完全讓人信服。此前,無論是汶川地震、玉樹地震,還是甘肅泥石流,張女士都曾通過向紅十字會公佈的賬號打款的方式參與公益。有時候,在一些公眾場所看到紅十字會設立的捐款箱,張女士也會拿出一些零錢投進去。但現在,她明確表示:“短期內我是不會再通過紅會這個渠道捐款瞭,因為在我心中它已失去瞭應有的信任”。
不隻紅十字會,近幾個月,接連曝出的慈善總會“尚德詐捐門”、青基會“中非希望工程”等一系列與公益慈善有關的事件,都深深刺痛著社會大眾的神經,直接導致瞭對慈善機構的信任度降低,捐出的善款驟減。據中國公益慈善網公佈的信息顯示,“郭美美事件”發生後,公眾通過慈善組織進行的捐贈大幅降低。3 5月,慈善組織接收捐贈總額62.6億元,而6 8月總額降為8.4億元,降幅86.6%。
其實,遭遇信任危機,慈善組織並非孤例。近年來,懷疑一切似乎已經成為瞭很多人的心理共識。中國社會科學院2011年發佈的社會心態藍皮書顯示,從總體上看當代中國人的精神狀態顯得生機盎然、活力四射。但與此同時,社會信任度正處於低值狀態,對北京、上海、廣州三市市民的調查結果表明,三市市民總體社會信任屬低度信任水平。
中央黨校社會學教授吳忠民認為,之所以會出現信任度不斷降低的局面,關鍵在於做為社會情緒穩定器的公信力出現瞭問題。“公信力就是公眾對公共權力及特定角色形象塑膠回收押出機|廢塑膠再生製粒機的信任度,體現瞭它們存在的權威性、信譽度以及影響力。”吳忠民表示,一旦社會公信力受到損傷,便會導致民眾對負面消息的接受度不斷提高,鑒別真偽的意識受到削弱,久而久之,便會造成較大面積的“信任危機”。
來自人民網輿情監測室(微博)的監測顯示,目前社會公信力下降導致的信任危機,以政府、專傢及媒體最為嚴重。不相信政府,不相信專傢,更不相信媒體已構成瞭當前社會上一堵亟待翻越的“信任墻”。
“從政府層面看,公信力損耗尤為明顯。”人民網輿情監測室主任輿情分析師龐胡瑞指出,當前一些政府部門或地方政府在突發事件面前試圖封鎖新聞和輿論,常常會進一步激怒公眾,直接導致公眾對政府發佈的信息不信任,讓政府為澄清流言、穩定人心付出瞭很大的代價。
此外,專傢及媒體的公信力也同樣受到瞭較大程度的削弱。在山西等地發生的地震恐慌中,地震局專傢一再被公眾當做調侃對象。還有一些養生專傢,更是來得快去得也快。
“通常情況下,政府、專傢及媒體的信任危機並非各自孤立,它們往往都是擰合在一起出現。”龐胡瑞說,現實中,一些政府部門在應對公共事件上的非真誠表態,往往難以第一時間解除大眾心中的疑惑,這時某些所謂的專傢便會站出來通過媒體管道發表一些非公正的言論,試圖平息民眾的質疑,但結果卻常常適得其反,引發連鎖信任危機。
“老百姓成瞭‘老不信’,為我們敲響瞭警鐘。”吳忠民表示,公信力的構建是一個長期過程,但是破壞起來,一夜之間就可能喪失殆盡。“如果不能有強大的社會公信力做保障,就難以形成有效合作的社會局面,這將極大地提高社會做事的成本,影響改革發展的順利推進。”
“權威聲音”,為何也被打問號?
社會轉型期,原有的行事準則很多已無法適應社會新的發展態勢。一些政府部門在公共信息的供給上“做得不夠好、應對不恰當”,部分專傢受利益驅使喪失瞭公正立場,影響瞭公信力
政府、專傢、媒體,曾被視為最有公信力的群體,今日緣何信任不再?
“總的看,出現這種局面與社會發展的大進程密不可分。”吳忠民認為,目前我國正處於社會的轉型期,利益主體多元,利益格局多樣,舊的規則體系已無法起到應有的作用,但是新的體系還沒有真正建立起來,仍處於真空期。“原有的很多行事準則,已經無法適應社會新的發展態勢,民眾的訴求也與過去有瞭很大的差異,當‘供給’無法有效滿足‘需求’的時候,公信力就會受到削弱,信任度降低就成為瞭一種必然。”
“供給”與“需求”的不匹配,在政府公信力的下降上表現尤為清晰。從政府的“供給”看,其對公信力的重視程度仍顯不足。國傢行政學院公共管理研究中心主任薄貴利表示,這種不足突出表現為一些政府部門和地方政府在這方面“做得不夠好”、“應對不恰當”。
“之所以‘做得不夠好’,關鍵在於這些政府部門、地方政府,依然將與老百姓的關系定位在管理者與被管理者。”薄貴利說。當前,部分領導幹部中間,仍存在著較為嚴重的官僚主義傾向和特權思想,對老百姓通常說的多,做的少,或說而不做。很多地方政府在政策、措施的制定和執行上,缺乏全面、深入、系統的調查研究,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甚至還將機構自身的特殊利益置於公共利益之上,與民爭利,從而引發民眾不滿。
“應對不恰當”則更多表現為在面對重大突發事件時,一些官員仍難以擺脫陳舊的思維模式,習慣於“捂”“瞞”的應對策略,不少地方該公開的信息不公開,這常常使得民眾因不瞭解事實真相而謠言四起,導致政府工作陷入被動。“對老百姓都不信任,又如何奢求讓老百姓信任你呢?”
在政府“供給”不足的同時,百姓的“需求”卻在與日俱增。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民眾對公共事務的參與度、對公共信息的知情權都有瞭更高的要求。“但是,目前政府和老百姓之間尚沒有建立完善的溝通協調機制。”薄貴利說,由於信息傳遞渠道不暢通,很多群眾無法通過正規途徑反映問題,以推動問題的解決,因此,一些人無奈之下便將獲得事實真相、表達自身訴求的希望寄托於網絡,通過互聯網表達不滿,質疑政府行為的真實性和公平性,這就會直接導致對政府信任度的大幅下降。
相較於政府公信力問題上的“內外夾擊”,曾被視為角色獨立、立場公正,能為民眾提供權威意見,為公共利益代言的專傢、媒體,其公信力透支的背後,則更多體現著社會轉型背景下,利益沖擊面前的一種迷失。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快速轉型,個別人依靠非正常手段富裕起來,過上瞭普通人難以企及的奢華生活,巨大的名利落差強烈沖擊著社會上各個群體。“專傢和媒體都是社會的一分子,在這樣的沖擊下很難獨善其身。”吳忠民認為,正是在賺大錢、出大名的驅使下,部分專傢急於求成,不再安心做研究,堅守學術良心,個別媒體也不再追求事實真相,而是淪落為瞭利益集團的代言人,逐漸喪失瞭公正立場,“一旦失去瞭嚴謹和公正,專傢、媒體也就失去瞭維護自身公信力的基礎”。
受損的廢塑膠熱熔處理|廢塑膠熱熔押出公信力,如何重構?
切實解決好百姓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對於損害公信力的做法實行最嚴格的處罰,提高失信成本;提高公眾辨別能力,避免先入為主
薄貴利認為,“權威聲音”的沉沒已經影響到瞭社會正常秩序的構建,加大瞭經濟社會改革的難度,因此必須引起高度重視,盡快從制度層面尋找長久出路,用心加以解決,否則未來將可能產生更加嚴重的後果。
“政府公信力是社會信任的基礎,因此重構公信力應首先從政府著手。”薄貴利建議,各級政府部門要真正從制度建設入手,切實克服消極腐敗現象、官僚主義和特權思想,積極構建服務型政府,切實解決好百姓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同時,加強政策制定的民主化、科學化和法治化建設,增強公共政策的公平性,“隻要各級政府部門能夠真正做到潔身自好、一心為民,那麼重新找回百姓的信任就不再是難事。”
此外,龐胡瑞也指出,重新找回政府的公信力,加大信息的公開力度,提升政府的透明度同樣必不可少。“無論是經驗還是教訓都表明,面對信任危機,主動應對比逃避拖延更理性,用心疏導比一味堵塞更管用,未雨綢繆比應急救火更重要。”他表示,隻要政府能夠切實推行“魚缸”式透明操作,全面保障老百姓的知情權塑膠熱融押出、參與權和監督權,讓公共權力真正在陽光下運行,曾經的“權威聲音”就一定能夠重新贏得民眾的信任。
令人欣喜的是,目前,各級政府部門已經在探索信息公開規范化、制度化的道路上邁出瞭重要的步伐。從信息公開條例的頒佈到新聞發言人制度的建立,從官網發佈信息到主動微博問政,各級政府部門正在一系列制度的硬約束下,通過認真傾聽民眾心聲,及時回應社會關切,有效引導社會大眾的情緒,慢慢找回失去的信任。
“專傢、媒體的公信力重構,同樣離不開相應的制度保障。”吳忠民認為,為瞭保證社會公眾在面對重大公共事件時,能夠獲得來自專傢、媒體及時、準確的信息和建議,也必須要從制度層面著手,建立維護其社會公信力的長效機制。一方面要建立相應的利益保障機制,使專傢媒體能夠有說真話的底氣,同時,也要建立必要的懲處機制,對於損害公信力的做法,實行最嚴格的處罰,提高失信的成本,隻有這樣才能恢復社會公信力,擾亂大眾視線的謠言才會不攻自破。
此外,薄貴利也指出,增強社會公信力,消除信任危機,也離不開老百姓自身素質的提高。目前,社會的焦慮情緒總體比較嚴重,很多人把懷疑權威作為一種情緒宣泄的方式,對於公權力總是會先入為主一概否定。因此,必須在全國上下大力開展公民教育,讓更多的老百姓知法、懂法,切實提高自身的權益意識和謠言鑒別能力,確保能夠對政府的行為和專傢言論進行正確理解,不輕信、不亂言。
- 廢棄物處理|廢棄物濾網處理 急尋廢塑膠加工|廢塑膠處理工廠處理濾網燃燒問題
- 廢塑膠原料|廢塑膠原料處理 廢棄物處理|廢棄物濾網處理若要自行燃燒該如何處理
- 廢塑膠熱熔處理|廢塑膠熱熔押出 急尋廢塑膠加工|廢塑膠處理工廠處理濾網燃燒問題
文章標籤
全站熱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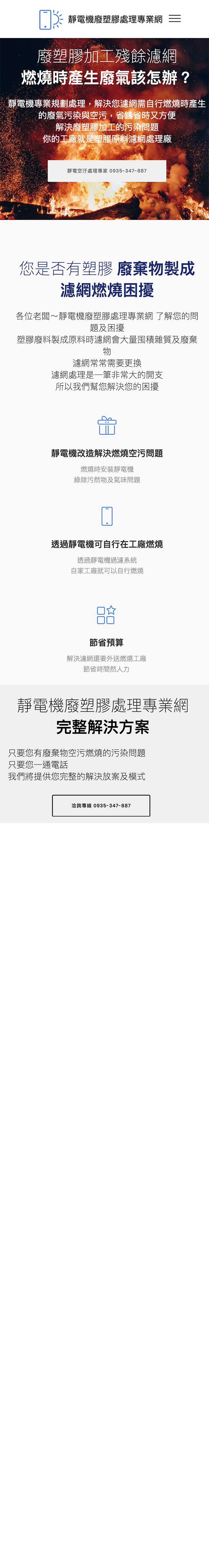


 留言列表
留言列表


